2025書業趨勢分析與展望
我們(men) 可能要接受書(shu) 業(ye) 市場端持續下行的現實了。
出版轉製國企稅收優(you) 惠政策得以延續、全民閱讀的推進力度仍在持續加大、圖書(shu) 生產(chan) 端仍保有較大規模……這些利好消息無疑提振了行業(ye) 的信心。
變化也一直在發生。人工智能所帶來的新一輪技術浪潮同樣在出版業(ye) 掀起了波瀾,中信出版、果麥文化等出版“大廠”均已投入其中;圖書(shu) 品牌化成為(wei) 大眾(zhong) 出版市場的趨勢,多家出版機構強化了旗下產(chan) 品線的品牌化力度;文創、穀子成為(wei) 熱門板塊,上海書(shu) 展變身文創展、“穀子經濟”驅動資本市場增長,也讓書(shu) 業(ye) 看到了相關(guan) 板塊的潛力;課後服務成為(wei) 地方出版集團轉型的重要抓手,多家地方出版集團將之視為(wei) 頭號工程;市場教輔的爆發式增長令人矚目,與(yu) 投流書(shu) 一起托舉(ju) 起零售市場的體(ti) 量;渠道的變革一刻也沒有停歇,書(shu) 業(ye) 對視頻號、小紅書(shu) 這些內(nei) 容平台的爆發天然地敏感,一有跡象就會(hui) 一擁而上……
市場的凜凜寒意也被絕大多數從(cong) 業(ye) 者所感知。2024年下半年以來,多數出版機構的反饋都是“每況愈下”,有資深出版人喊出,這是從(cong) 業(ye) 以來最難的時候。數據可以佐證。開卷數據顯示,2024年總體(ti) 圖書(shu) 零售市場碼洋同比下降1.52%,總體(ti) (不含教輔教材)市場碼洋同比下降4.83%。總體(ti) 圖書(shu) 零售市場碼洋規模1129億(yi) 元,恢複到2019年的88%。中金易雲(yun) 數據顯示,2024年圖書(shu) 市場碼洋為(wei) 1111.64億(yi) 元,同比下降10.50%;當剔除文教類的剛需產(chan) 品後,其他大類圖書(shu) 銷售同比下降17.23%。綜合來看,不僅(jin) 圖書(shu) 零售市場規模連續出現下滑,作為(wei) 出版業(ye) 基本盤的教育出版也麵臨(lin) 挑戰——評議教輔的監管政策日趨嚴(yan) 格,人口紅利的消退也讓教育出版市場的前路變得越發難測。
不僅(jin) 如此,市場下行的不良反應已經開始向出版全產(chan) 業(ye) 鏈蔓延——經銷商爆雷、出版機構縮減品種和人員規模、中小型圖書(shu) 公司現金流緊張成普遍現象、文化紙廠家訂單近乎負利潤、許多印廠機器空置……
回顧過去幾年裏各書(shu) 業(ye) 媒體(ti) 的盤點總結,從(cong) 業(ye) 者們(men) 已經對“拐點”“迷茫”“邏輯崩塌”“經驗失效”等諸多關(guan) 鍵詞脫敏,但到了當下這個(ge) 節點,所謂的“盤整期”已經是一種樂(le) 觀表達方式,在認知層麵,出版人或許要做最困難的準備了。

困境
市場體(ti) 量下滑的背後,是出版人遭遇的多方麵的困境。
渠道亂(luan) 象已經到了讓書(shu) 業(ye) 無以為(wei) 繼的地步。折扣隻是一個(ge) 老問題。過去,傳(chuan) 統電商平台疊加了優(you) 惠券、滿減等政策,圖書(shu) 的實際銷售折扣在數據統計時體(ti) 現得並不明顯。內(nei) 容電商的崛起進一步拉低銷售折扣的同時,也讓折扣數據更直觀地體(ti) 現出來。開卷數據顯示,2024年1-11月,少兒(er) 類、社科類、文藝類圖書(shu) 在內(nei) 容電商的銷售折扣分別為(wei) 36%、42%、47%。這一組數據相比整體(ti) 市場的圖書(shu) 銷售折扣更具參考價(jia) 值。再考慮到流量費用和銷售傭(yong) 金,也更殘酷地體(ti) 現了圖書(shu) 在內(nei) 容電商平台的利潤空間。
不僅(jin) 如此,和其他消費品類似的是,在內(nei) 容電商渠道,圖書(shu) 的流量生意也成為(wei) “白牌”絞殺的戰場。過去兩(liang) 年裏,內(nei) 容電商的圖書(shu) 品類湧入了諸多“流量玩家”,他們(men) 利用流量玩法和資金優(you) 勢,通過買(mai) 斷版權拉高圖書(shu) 定價(jia) ,壓低圖書(shu) 折扣,跑量投流。這種流量生意要求出版機構既要在組織結構上有極強的快速反應能力又要有極致的成本壓縮能力。因此,受限於(yu) 版權與(yu) 印製成本、內(nei) 容調性和原有的渠道優(you) 勢的傳(chuan) 統出版機構,不論是國有還是民營企業(ye) ,幾乎都無法染指。這類公司往往選擇剛需性強的少兒(er) 和教輔圖書(shu) 作為(wei) 主營品類,以大量生產(chan) 雷同內(nei) 容進行測試的方式,找到適配算法傾(qing) 斜的產(chan) 品,既改變了消費者對圖書(shu) 折扣的認識也抬升了算法的流量費用。在激烈的競爭(zheng) 之下,這門生意也越來越不好做:許多公司從(cong) 一開始的薄利多銷到投流微虧(kui) ,寄希望於(yu) 流量能溢出到其他平台,再到現在,已經將圖書(shu) 定位成課程、谘詢等高客單價(jia) 產(chan) 品的引流品,靠流量賣書(shu) 的利潤空間也越來越狹小。除此之外,這類產(chan) 品往往以高定價(jia) 的套裝形式出現,抬高了整體(ti) 市場的碼洋規模,表麵上托舉(ju) 了市場體(ti) 量,在碼洋數據統計層麵緩衝(chong) 了圖書(shu) 市場的下行,實際上卻給多數出版機構製定增長目標提供了錯誤的判斷依據。如果去除開卷數據統計中“內(nei) 容電商銷量占比超過90%”的圖書(shu) 產(chan) 品,再來看市場規模,數據顯示,去除這部分產(chan) 品的銷售數據後,2023年開卷監測的圖書(shu) 零售市場碼洋規模為(wei) 664億(yi) 元,2024年1-11月的這一數據則為(wei) 658億(yi) 元;與(yu) 之對應的是,2019年開卷統計的數據為(wei) 1286億(yi) 元。這或許可以大致體(ti) 現出圖書(shu) 市場下行之後真正體(ti) 量。
把眼光放到產(chan) 品端,長銷品和腰部書(shu) 的衰退更值得警惕。電商平台的圖書(shu) 榜單在失效,閱讀推薦的核心也從(cong) 閱讀推廣人轉變為(wei) 以銷售為(wei) 目的的主播。因此,過去許多年裏出版機構賴以生存的長銷產(chan) 品和作為(wei) “現金奶牛”的經典圖書(shu) ,在這一輪渠道洗牌當中被大量淘洗出局,新的品種又很難在短視頻電商這種容量小、銷售周期短的渠道裏迅速成長為(wei) 銷售主力。圖書(shu) 市場的銷量結構也出現了分化,二八定律不再適用。開卷數據顯示,2024年1-11月銷量前1%的品種對應碼洋貢獻達61.9%;銷量前5%的品種,碼洋貢獻高達83.7%,相較於(yu) 2023年,這兩(liang) 個(ge) 比例都有所提升。滯銷書(shu) 也在擴大,《出版人》在2024年的一篇稿子裏分析道,2019年至2023年圖書(shu) 零售市場銷量數據中,年銷售數量小於(yu) 5本的圖書(shu) 平均占全部圖書(shu) 品種的34.3%;年銷售數量小於(yu) 10本的圖書(shu) ,平均占全部圖書(shu) 品種的43.8%;2023年銷量小於(yu) 10本的圖書(shu) 超過百萬(wan) 種,這無疑指向腰部圖書(shu) 的衰退。出版業(ye) 尤其是大眾(zhong) 出版賴以生存的“風投機製”開始失效,長尾效應正在失效,書(shu) 業(ye) 生產(chan) 係統的平衡被打破,品種冗餘(yu) 的生命力轉化成了產(chan) 能過剩的負擔。
這一現象也給整體(ti) 市場帶來了極強的不確定性。雖然圖書(shu) 零售市場是一個(ge) 典型的供給側(ce) 驅動市場,但是市場鏈條一直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如今,出版機構的茫然有很大一部分來自經營確定性的缺失。
合作夥(huo) 伴是不確定的。有的經銷商因為(wei) 經營不善留下一筆呆壞賬,有的因為(wei) 不想再守著圖書(shu) 微薄的利潤而轉行;一年前辛辛苦苦建聯的1萬(wan) 個(ge) 達人裏,可能有8000個(ge) 來年就不賣書(shu) 了,頭部達人正在放棄了圖書(shu) 業(ye) 務……業(ye) 績是無法規劃的。閱讀的需求在轉移,做新書(shu) 越來越難,根據中金易雲(yun) 的數據,出版機構隻要賣出1.1萬(wan) 冊(ce) 左右的書(shu) ,就能進入整體(ti) 市場銷量的前1%。市場的量會(hui) 從(cong) 何處來無法預估,算法的眷顧是一個(ge) “黑箱”,一條短視頻就可能引爆一本書(shu) 的銷售。但這種爆發又是速朽的,開卷監測《我們(men) 生活在巨大的差距裏》這本老書(shu) 在2024年實現了近三百萬(wan) 的銷量,峰值月銷超過70萬(wan) 冊(ce) ,但是僅(jin) 僅(jin) 半年後月銷量下滑到不足3萬(wan) 冊(ce) ,這樣的大起大落可能非常考驗決(jue) 策者的心髒和機構的投流費用。
頭部出版機構在內(nei) 容端必然追求更強的確定性,例如到期的暢銷書(shu) 版權拍出高價(jia) ,把公版書(shu) 玩出新花樣,大舉(ju) 進軍(jun) 熱門品類並以此擴大規模,提升老書(shu) 的運營力度。中小型出版機構則盡一切可能降低風險,壓縮品種規模,壓縮人員規模,大眾(zhong) 出版的中小型圖書(shu) 公司的最終歸宿可能就是小工作室或者個(ge) 體(ti) 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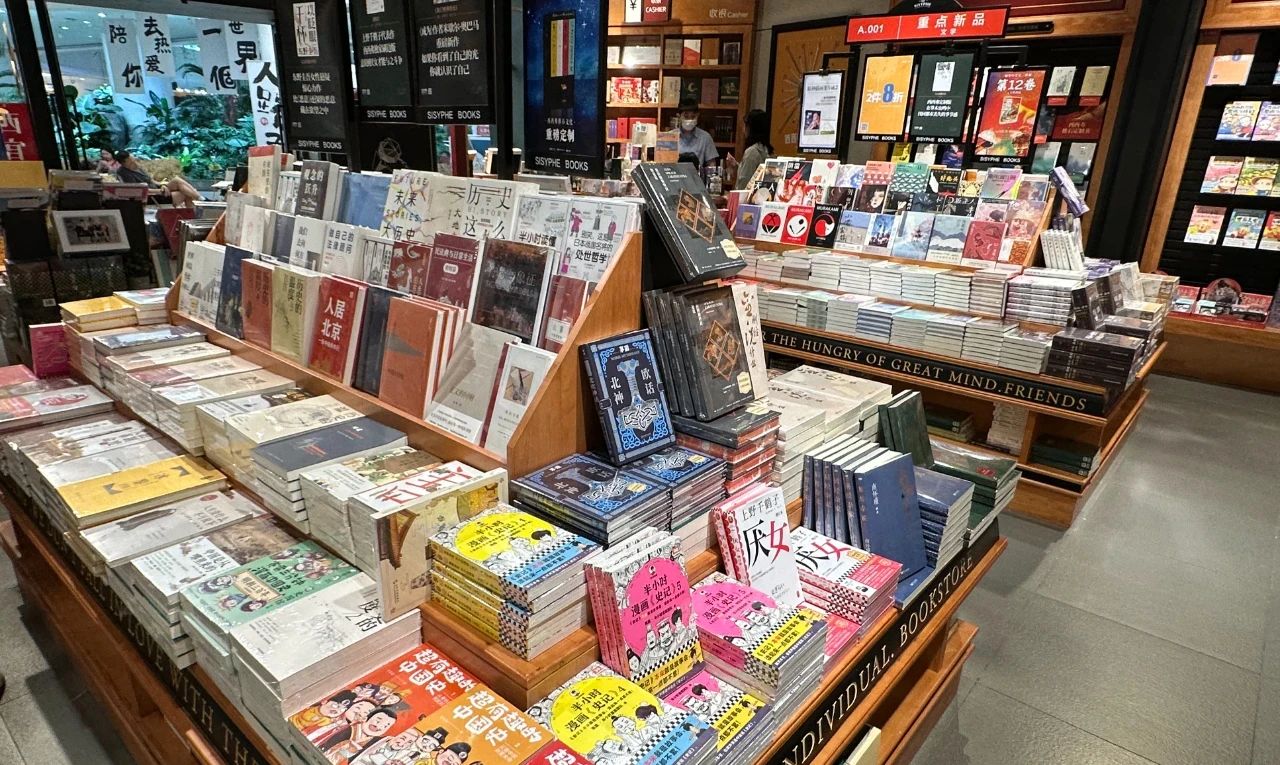
可以說,在當下,書(shu) 業(ye) 的出品係統和銷售係統都遭遇了極大的調整,品種規模和碼洋規模都失去了意義(yi) 。回到業(ye) 務去審視,書(shu) 業(ye) 從(cong) 一個(ge) 創意、創造型產(chan) 業(ye) ,幾乎已經變成了勞動力密集型、生產(chan) 型產(chan) 業(ye) ,出版業(ye) 越來越像製造業(ye) ,享受不到內(nei) 容、版權的紅利,利潤微薄,但是又無法以銷定產(chan) 。版權不屬於(yu) 出版機構,要麽(me) 是作者的,要麽(me) 是海外出版機構的,因此版權衍生的商業(ye) 開發出版機構自然也無力涉足;在用戶端,出版機構也沒有主動權,用戶數據被互聯網平台所掌握。不論是對上遊作者的創作支持,還是對用戶的增值服務,多數出版機構都無法提供。
代價(jia)
市場下行與(yu) 書(shu) 業(ye) 底層邏輯的坍塌互為(wei) 因果,共同指向了書(shu) 業(ye) 諸多不可承受之痛。
首當其衝(chong) 的是書(shu) 業(ye) 的管理模式亟需優(you) 化。
一方麵是考核不科學帶來的動作扭曲。當下,碼洋作為(wei) 行業(ye) 通行多年的單位,已然失去了統計價(jia) 值,但是仍有不少出版機構將發貨碼洋和回款的絕對值作為(wei) 考核的主要指標。這也導致了“超發超結”成為(wei) 不少出版機構的應對手段。過去兩(liang) 三年,因為(wei) 業(ye) 績壓力陡增,部分出版機構“超發超結”的力度進一步加強,有的出版機構甚至在11月就已經預結第二年第一季度乃至上半年的銷售回款。除此之外,過去書(shu) 業(ye) 的賬期普遍在一年以上,如今由於(yu) 內(nei) 容電商的崛起,賬期被壓縮到3-6個(ge) 月,某種程度上也致使出版機構未來業(ye) 績被提前透支。
當市場處於(yu) 上行階段時,這種“寅吃卯糧”的方式並不會(hui) 有負麵影響,甚至會(hui) 驅動出版機構不斷增長。問題在於(yu) ,當增長不再,那些在年底“懟”出去的貨又將如何消化?一家出版社的發行人員在盤庫時發現了一年前發出的貨原封不動地被退回,包裝都沒拆,隻能淪為(wei) 直播間的引流瑕疵品。不僅(jin) 如此,“超結”也是要付出代價(jia) 的,不論是提高返點還是降低銷售折扣,都會(hui) 壓縮出版機構的利潤空間。可以預計的是,如果市場形勢沒有發生變化,出版機構的業(ye) 績壓力會(hui) 進一步加大。2025年,可能有部分機構會(hui) 麵臨(lin) 一季度甚至上半年“淨發為(wei) 負、回款為(wei) 零”的危機。
這實際上是短期考核帶來的矛盾。國有出版機構肩負著國有資產(chan) 保值增值的重要任務,勢必要完成特定的指標任務,但是在實際考核中很難評估出版作為(wei) 創意型產(chan) 業(ye) 的可持續發展指標,因此出版的長期主義(yi) 就非常仰賴管理者本身的眼光、能力甚至是道德品質。對於(yu) 中小型民營公司而言,雖然沒有實質性的考核指標,但是普遍現金流緊張,迫於(yu) 生存壓力也很難做長遠布局。
另一方麵是出版企業(ye) 製度性的落後。時至今日,“一本書(shu) 的實際盈利”對於(yu) 多數出版機構來說仍然是一筆糊塗賬,出版機構往往既算不清楚成本也監測不了實銷,同時在機構體(ti) 外有大量的“僵屍庫存”。缺乏零售能力的出版機構困在一個(ge) 個(ge) B端客戶裏,在各類條款上受製於(yu) 人,尤其是麵對電商平台時,既掌握不了定價(jia) 權又被隨意退貨。
轉型的遲緩也讓出版業(ye) 麵對需求轉移時缺乏工具。很遺憾的是,出版業(ye) 在過去日子比較好過的時候,並沒有真正解決(jue) 轉型方向的問題。轟轟烈烈的“數字化轉型”並沒有給營收業(ye) 務帶來新的支撐點;自研內(nei) 容也鮮少培育出成熟團隊,IP研發也主要是“拿來主義(yi) ”;由於(yu) 缺乏並購路徑,市場上也沒有出現能夠與(yu) 平台抗衡的集團或者聯盟;對比海外出版集團商業(ye) 模式的轉型,國內(nei) 出版轉信息服務、出版轉教育、出版轉娛樂(le) ,也未見有明顯的跡象。
這些無疑都是危險的信號。出版的價(jia) 值仍舊存在,依然承載著人類文明進步和文化傳(chuan) 承的使命,但是出版機構的日子可能不好過了,正如著名出版人佘江濤公眾(zhong) 號的一篇稿件裏所說的:“出版有未來,出版社不一定。”出版機構應該如何思考未來,找到生存路徑?
何解?
無論如何,分化已經到來,如何迎接新的市場結構與(yu) 業(ye) 務邏輯?我們(men) 走訪了許多出版人,收獲了幾個(ge) 關(guan) 鍵詞。
調整預期。對於(yu) 書(shu) 業(ye) 而言,經曆了21世紀頭二十年的高速增長,麵對市場可能持續的下行,從(cong) 資產(chan) 管理方到管理層再到業(ye) 務一線,或許都要適應新常態,重新調整預期。對於(yu) 機構而言,如何從(cong) 追求量的絕對增長轉向質的可持續發展,將成為(wei) 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精準。這是一個(ge) 被出版機構頻繁提及的方向,選題和營銷的精準將成為(wei) 基本要求。因為(wei) 市場通道狹窄,泥沙俱下、草莽發展的內(nei) 容生態不複存在,“拍腦袋”和“微操”帶來的傷(shang) 害可能比之前要大許多,盲目的選題決(jue) 策和跟風的代價(jia) 出版機構將難以承受。對於(yu) 出版機構而言,當腰部的價(jia) 值不再,可能需要重新思考自身的使命與(yu) 定位——要麽(me) 追求一年出10本書(shu) 改變世界;要麽(me) 做100本有精準用戶與(yu) 流量保障的書(shu) ,在極其細分的領域裏擁有定價(jia) 權,品牌化就是路徑。這是一道選擇題,也可能根本沒得選。營銷的精準在於(yu) 出版機構設置議題、引領輿論的能力逐漸式微,從(cong) 過去放衛星、“雨打沙灘萬(wan) 點坑”的營銷方式變成了帶著內(nei) 容敲開一個(ge) 個(ge) 小型會(hui) 議室。當經典圖書(shu) 的共識消退,營銷的精準也承載著重塑經典的使命。如今一代人的經典圖書(shu) 正在逐步退出曆史舞台,垂直細分領域的圖書(shu) 需要新的生態位構建。行業(ye) 從(cong) 來不缺優(you) 質的內(nei) 容,但是優(you) 質內(nei) 容如何響應這一代人對於(yu) 國家、社會(hui) 乃至個(ge) 人關(guan) 鍵議題的認知需求與(yu) 情緒需求,需要營銷的介入。果麥對《窄門》的營銷是一個(ge) 值得關(guan) 注的案例——一本100多年前的小說被塑造為(wei) “純愛”作品,並收獲相應的銷售回報,這也是通路。
回歸人本身。人工智能所描繪的未來圖景還未完全展開,但是這一年的噪聲已經讓各行各業(ye) 感受到了技術浪潮的勢能。對於(yu) 書(shu) 業(ye) 機構而言,必然要充分跟進技術變革的趨勢。但是追逐的目的是什麽(me) ?過去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們(men) ,不能指望這個(ge) 老行當真正駕馭技術浪潮,那麽(me) 技術革命中區分人與(yu) 機器的邊界,重新找到“出版人”的定位,就變得尤為(wei) 重要了。那些人工智能做得很好的,人力就應該轉向,讓位給效率與(yu) 成本。對於(yu) 出版機構而言,最終還是要回到出版人本身,這個(ge) 行業(ye) 說到底是人的事,因此,如何在組織結構和激勵機製乃至業(ye) 務方向塑造平台以聚攏超級個(ge) 體(ti) ,釋放創意效率與(yu) 商業(ye) 能力,或許是大型出版集團的方向。

跳出出版。需要承認的是,圖書(shu) 距離內(nei) 容消費的中心越來越遠了,新一代人在接觸紙書(shu) 之前,已經被包括短視頻、遊戲在內(nei) 的其他內(nei) 容形式馴化過了,等他們(men) 成長起來,還真的會(hui) 愛上閱讀嗎?這或許是存疑的。現在來看,“穀子”、二次元、文創這些概念層出不窮,過去許多小眾(zhong) 的內(nei) 容消費需求已經成長為(wei) 主流了。出版機構也是時候跳出出版,更換話語係統,再重新思考如何去抓住未來這一代人的閱讀需求,才有真正的一席之地。
無論如何,書(shu) 業(ye) 有其韌性,也有其核心價(jia) 值和自身邏輯,終究會(hui) 跨越周期,重塑產(chan) 業(ye) 生態。而在當下,向新而行、步履不停遠比坐在屋裏做樂(le) 觀和悲觀推測更有價(jia) 值。
本文選自《出版人雜誌》,原文標題《2025,書(shu) 業(ye) 在寒意中迎來分化》
